晚近广州,既是政治革命的发源地,也是文明转型的试水区。百年风云,如白驹过隙,沉淀在历史记忆里的,既有雄姿英才的宏大叙事,也有小桥流水的生活细节。有时,触动人心的,反而是那些不起眼的大城小事———“城记:近代广州细节”要呈现的,正是一幅晚近广州的“清明上河图”,详细、细碎,小处见大,复原这座烽烟城市的热辣镬气。
民国时期,茶楼给广州市民生活提供了很大的方便,鲁迅把茶楼的作用概括为:“打听旧事,闲读心曲,听听说书”。茶楼和市民生活严密地联络在一同。以茶楼为管窥,我们可以看到民国时期广州市民生活的部分相貌,了解到社会转型时期的民众生活。
日常生活在茶楼
茶楼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所以在社会政局相对安宁,经济得到长足发展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茶楼快速发展,达到了民国时期的鼎盛阶段。
茶楼中的饮食效劳内容首先便是茶水,茶叶有普洱、水仙、龙井……相比而言,茶楼中的茶水是较好的。较早出现的低级的二厘馆、粉面馆等地方提供的茶水往往很粗劣,茶叶是一种被泡过屡次后晒干加工而制成的翻渣茶叶,“人唾狗溺,坑脏不堪”。
饼食、小食是茶楼中吃的内容。“点心有虾饺、烧卖、叉烧包等”,“点心是由茶倌用大蒸笼拖来售卖的,新颖味美,热腾腾”,这些小食价格没有糕点那么昂贵,还可以抵饱,所以深受客人欢迎,很多人一日三餐即以此为食。在西关的仁昌茶楼,人们很早就在那里等候,食品出笼之时,“茶客纷纷离座,次序大乱,众茶客不俟分派,争先攫取,眼疾手快,得取一二个,笑嘻嘻,其伸手待取者,仍环绕蒸笼,肩背撕磨,极端拥堵,十足似群丐争举瓦休待施样子,霎时即攫取无余,落空者也不乏其人,廖然返座,无精打采,攫得者,捧饱大嚼,左顾右盼,栩栩有色,尤令攫不得者垂涎,待第二笼出锅,茶客又会争抢如前。”虾饺也是茶楼中广受欢迎的食品,在漱珠茶楼,“恒有泡茶坐候虾饺者,故蒸笼甫上,茶客即阙可是上,百手齐下,争先攫取,如恶鬼夺食,稍一耽搁,蒸笼已空无一切”。
饼食糕点是茶楼区别于其他饮食单位的一个重要内容,“饼食有油蛋散、薄切酥、云片糕”,还有至今耳熟能详的陶陶居月饼、莲蓉饼、小凤饼……由于竞争的剧烈,茶楼持续推陈出新,挖掘了众多点心精品。以月饼为例,到1927年,广式月饼已达80个品类,称号各异,如七星伴月、双黄莲蓉月、五仁甜肉月、叉烧火腿月、唐皇燕月等。
茶楼的环境卫生已有一定的改观,通常是“玻璃台面,四旁亦玻璃,可以窥见台中的种种食品,此种设置较为有益卫生”。
从自然生态环境的角度讲,广州地处岭南,气候闷热,出汗较多,能量耗费大,饮茶可以生津止渴,吃点心则符合多餐少食的习惯,有助于能量的及时补充,所以上茶楼喝茶很大程度上是人体生理需求。而更重要的则在于茶楼给民众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人们的生活差不多和茶楼融为了一体。
文娱休闲在茶楼
民国时期的广州,虽然已经有了剧院、电影院、歌舞厅等文娱场所,但关于大大部分普通市民来说并不是可以常常光临的,而茶楼则可以提供相对廉价的文娱方式和场所,人们只需多花几分茶钱便可以很容易在茶楼听曲、遛鸟、赌博等,而且时间上很广泛,差不多无所限制。
说唱这种中国传统的艺术方式,似乎和茶馆有一种天然的联络,北京的茶馆甚至就叫茶园,和梨园相对应,专门设一登台供唱戏所用,喝茶反倒成了副业。成都茶馆也有类似状况。在民国广州茶楼中,先是出现了“瞽姬”,随后又有了女伶,她们为茶客们带来了无限乐趣,更为粤曲的传播做出了很大奉献。
瞽姬出现较早,清同治时期已有,她们的身世往往都很凄惨,从小受尽磨练,学艺成功后,就成为收养她们的人的摇钱树。随着茶楼酒肆的大量出现,瞽姬出如今了这些场所,风行一时。到1920年,“西关长命大街朱冠兰始雇省府著名瞽姬……茶客耳目口腹兼收并蓄,趋之若鹜,继而十八甫真光天台专设顾曲台,几以买曲为主业,而茶点为副业。”瞽姬给茶楼带来了不小的利润,也给那些爱听曲之人带来了无限乐趣,那时珠江两岸还没有桥梁架设,这些人甚至“由河南渡河北听曲,深夜归时,长堤一带之人,惟己影云云”。但瞽姬的缺陷在于不能和茶客进行较好的交流,女伶则克制了这个不足,“女伶能以目看以眉语,瞽姬不能,女伶可以与客人周旋,瞽姬不能”,所以,上世纪20年代初,女伶出现后逐步替代了瞽姬。
女伶一经出现便大受欢迎。那些爱好女伶者,大肆追捧。一些著名的女伶如白玉梅、文仔、银彩、燕燕、梅影等更是惹起那些嗜好者的热捧,为此还构成了不同的派系,如“郭湘文党,公脚秋党,白燕仔党”等,各派中各阶层人士都有。1925年,《广州民国日报》专门开拓《歌坛燃犀录》一栏,不断性地对茶楼唱曲女伶介绍品评,当然对此也多有批评,但这正好反映了那时的女伶唱曲之盛,影响之大。
女伶唱曲虽然遭到了不少人的欢迎,也为茶楼带来了一定的收益,但在地方当局来看,这项活动却是“有伤风化”,因而屡加不允许,后因“军饷源关系加以复开”,用征收女伶税的方法加以管理。社会精英们并没有饷源之忧,所以可以看到,报纸上的批评声音自女伶出现后就接连持续,他们指出了茶楼女伶唱曲的弊端:“为锣鼓喧天,争风呷醋场所”:“此风一开,弊端丛生,打架滋事之事时时发生”。报纸称那些热衷于女伶的人为“女伶大舅”,以为此类人士具有四个条件,即“无职业、厚面皮、善说谎、假殷情”,作者以为女伶移风易俗,而那些喜好女伶之人,日久必受其同化,因而,应该限制女伶。确实,在热衷于女伶的人群中,有这样一部分人,他们无所事事,整日四处追逐女伶,如一个叫做何指远的人,“跟随女伶左右,如卫兵然,捧茶献烟,皆克尽其职,女伶度曲必送之返家,如是数年,资历老且深矣,凡长女伶之茶居,无人不知,其银包常空空然,皆以应酬女伶”。
赌博这种恶习在近代中国非常普遍,但在休闲文娱贫乏的年代,它却是市民文娱的一种方式。近代广东赌博之风更甚,蔓延到茶馆中,赌博现象非常普遍,类型有斗蟋蟀、赌牌、斗雀……从表面上看,政府不断在厉行打击赌博,如1916年龙济光开始管理广州,上台伊始就发布告示称:“牌捐尤粤秕政,立予取消,往后如有假托官厅名义,私自擅收及再有牌赌发现情事,一经察觉,或被人揭发,均即严行惩治。”之后的历届政府也有类似言论,但实际上,赌博不断屡禁不止,其中的次要缘由就在于赌博涉及到很大的经济利益———赌税。所以致抗战前夕,赌税“居然成为地方财政一大支柱”。
抗战后的官方材料显示,为了不允许赌博,警察局屡次对茶酒楼等公共场所进行了调查,还让各茶楼写严禁赌博的保证书。“饬令确切查办各酒楼茶店等公共场所聚赌具报,应查明严峻取缔。”警察局发布命令让各酒楼茶店公共场所聚赌具报,并发布了相关茶酒楼的名单。
茶楼不仅和说唱等艺术方式密不可分,还和新出现的事物———公园相结合,出现了公园茶亭。广州出现公园后,一些精明的商家很快就看准了这个商机,如中央公园内便有泉隐公司承办茶亭营业,“以供市民文娱”。市府也看到了其中包括了一定的财政收入,所以广州市工务局建筑课曾就第一公园茶亭招商登载广告:“茶亭由呈商建筑最低建筑费为八千元;月租定价为一百三十元;期限五年,期满令投旧商得折回建筑物料。”公园和茶亭的结合更好地满足了市民紧张生活之余寻求放松的心思需求,“一帮朋友到公园,既可边喝茶边闲话家常,又可消磨光阴,增进感情,还可怡情养性”,所以,“好饮茶者乐此不疲”。
社交待客在茶楼
人都有交流的欲望,经过交流构成自己的人际网络,所以很多人上茶楼不仅仅是为了喝茶、听曲,他们更喜欢在这种良好的环境中闲谈、谈生意、交流情感……作家韦君宜对此很有领会,她称赞茶楼“像个群众的社交场合,氛围的确可爱,这点人情味实在令人愉快”。那时的报纸也说茶楼是“市民交际,品茗叙会之所”。而一位记者在报纸上刊文指出,人们上茶楼“甚有一日的工资就做一日的茶费”,作者深知这种恶习惯是不可以染的,坚持不饮茶,但近来与社会接触又觉得非茶楼不足与朋友畅谈心事,借茶楼与各同事周旋,联络感情,感情深沉时,可以相互帮助,所费有限,收益颇大,作者破了茶戒,与友人上诞香楼。可见,茶楼确实是实惠的社交场所,既省钱,又可以办好事。“有时远路亲友到访,约往品茗,以此来表达诚挚之意”,即在广州人看来,在茶楼待客是一种较高的礼仪。
茶客们往往习惯到一个地方品茗,“茶客乐于某茶楼者,虽一日数登而不厌,转登别楼,总觉有些不快”。大量熟客的存在是很多茶楼不断能生活下去的重要缘由,否则在剧烈的竞争中有的早已被淘汰。如瑞如茶楼之所以尚存,就在于“旁边商店同伴,菜贩尤喜光临,由于熟客仔之光临”。同一行业或同一类人喜欢积聚到一个茶楼,如长命新街朱冠栏茶楼,“往该茶楼品茗者多为熟客,一则为与茶堂倌谈笑,一则打听商业行情,高弹阔议,彼此互通音讯,该茶居之盛,不为无因”。“太如品茗者多本街银业中人”;一德路的源源茶楼,则是“小贩和海味行同伴习惯去的地方”;大北旁边的羲全茶居光临者多为“旁边种植农夫与磐石工人”;九记茶楼顾者多为“帮门坐食之人,及深夜不寝之道友,喧哗不休,怪状百出”。甚至,一些不法之徒也喜欢到茶楼密谋。1947年12月的一日,在中华中路汉记茶楼,几个人围在一同“浅斟低酌中,仍左顾右盼,神态机密”,显然他们是在进行着不可告人的密谋,警察抓捕审问后才知“与最近某大窃案有关”。而一些环境幽静的茶楼,则为知识分子所欢迎,如惠如茶楼的光临者多学界中人,他们经常“自居一房,开茶一盅,挟册观书,久而弗去,视此为休息之所也”。可见,同行往往聚到一同,这样很便于交流信息,了解行情,就是谈起话来也有更多的谈资,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在茶楼中也得到了很好地表现。
一些名人都曾对广州的茶楼记忆深刻,在他们的著作或回想中就屡次谈及广州茶楼。鲁迅先生在1927年任教于广州中山大学,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在短的几个月中,他和许广平等友人就曾屡次光临茶楼,如日记中记到“(1927年,下同)3月18日,雨,午后,同季市、广平往陶陶居品茗”,“3月26日,夜,同季市、广平往陆园饮茗”,“4月22日,并绍原、季市在宝汉茶店午饭”。巴金也曾上茶楼,并记下了在陶陶居遇见“睇相”的见闻。甚至有学校把课室搬到了茶楼,把茶楼由社交场所变成了教育场所。
◎李晓军,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讨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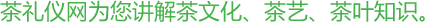




 喝茶敲桌子,是无礼还是有礼?
喝茶敲桌子,是无礼还是有礼? 茶,很慢
茶,很慢 茶艺四要——茶水火器
茶艺四要——茶水火器 茶虽同,味道却不同
茶虽同,味道却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