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茗”的审美属性与中国茶道的本质
那么显然,如果要称得上是“茶道”,就应该具备上述这样的存在特征。虽然这也只是停留在“是怎么样”而非“是什么”的层面,也就是说只是一种理想的预设。但是,以这种理想范型(Pradeiguma)为尺度,作为衡量“茶道”有无的标准,我们仍然可以探索在中国的茶文化中具备审美意义的“品茗”是否拥有“茶道”的内涵与本质。
从上述“道”所揭示的内涵来看,关于“茶道”应该具备两个方面的探索,那就是天道与人道。天道与“物”相关,属于“当然”之道。而人道则与“事”相接,是寻求“当为”之道。从上一节所分析的“品茗”审美属性中可以看出,从唐代至清代,有关茶文献中阐述的历代茶人对于品茗的各种心得、规约、讲究等,有一个明显的倾向,那就是都在揭示人与物的关系、即如何辨别茶、如何采摘、加工、保存茶、如何选水、如何煮水、如何点茶、选择怎样的饮茶环境等,表现的都是作为品茗主体人的存在如何面对人之外的诸物的存在,在这里“法自然”的追求是茶人们的共同特征。比如、强调好茶与采茶时节的关系、好汤与好水的关系、侯汤与茶人的关系、点茶心得等,都体现出这种倾向。这些“当然”涉及的都是“天地之道”、“自然之道”的问题,说明在中国茶文化的“品茗”审美中,构成“茶道”意义探索的其中一个方面的形式条件与表现内容是有所体现的。
那么,另一个方面之与人相关的“人道”探索是否存在呢?其实,在“品茗”审美中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上一节没有梳理,那就是关于“品茗”中“茶侣”选择的问题。而这正是构成“茶道”的另一个重要侧面、即人道之当为的问题。
“茶侣”指的是茗饮的宾客,所以在明代还出现“茶宾”的表现。“茶侣”一词最初出现在明代徐渭所改订勒石的唐代卢仝《煎茶七类》中,其中的“第六类”曰:“茶侣:翰卿墨客,缁流羽士,逸老散人,或轩冕之徒,超然世味者”。需要注意的是,此文献“七类”中的“第一类”首先讲“人品”问题,曰:“一、人品:煮茶虽凝清小雅,然要须其人与茶品相得。故其法每传于高流大隐,云霞泉石之辈,鱼虾麋鹿之俦(说郛续本,喻政茶书,把‘……之辈,鱼虾麋鹿之俦’一句半改缩成‘磊块胸次间者’)”。这个文献提供了两个信息:第一,如果此文献真是卢仝的作品,说明“茶侣”之说源自唐代(因其自序说此文献是其修订卢仝之作)。第二,关于“茶侣”的选择源于“茶”对于“人品”的要求,即所谓的“须其人与茶品相得”。正如屠隆所说:“使佳茗而饮非其人,犹汲乳泉以灌蒿莱,罪莫大焉。有其人而未识其趣,一吸而尽,不暇辨味,俗莫甚焉。”也就是说由于茶对于人的要求,在“品茗”时需要与之相宜的宾客。
徐渭(卢仝)的这种思想在宋代叶清臣《述煮茶泉品》也有所体现。曰:“紫华绿英,均一草也,清澜素波,均一水也,皆忘情于庶汇,或求伸于知己,不然者,丛薄之莽沟渎之流,亦奚以异哉!”在此文献的“跋”之中,更进一步提出了品泉如品人之说。[4]根据叶清臣的理解,茶叶与水,本来与“丛薄之莽沟渎之流”无异,由于人的发现而使其成为尤物。那么,“品茗”对于“茶侣”的选择,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在此后的许多茶文献中,都能看到关于“茶侣”相关的阐述。为此,屠本畯在《茶笈》中评曰:“茶犹人也,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
关于“茶侣”,除了这些对于品茗者的品性、修养、学识等要求之外,还有对于多少宾客人数的要求,这在前文已经述及张源在《茶录》中最初提出了人数多少为宜的问题,后来高元濬在《茶乘》中把“茶侣”与人数要求合在一起,专设“茶宜”一章阐述:“茶侣宜翰卿墨客,缁流羽士,逸劳散人,或轩冕之徒,超轶世味俱有云霞泉石、磊块胸次间者。(这些内容出自徐渭)饮茶以客少为贵,客众则喧,喧则雅趣乏矣。独啜曰神,二客曰胜,三四曰趣,五六曰汍,七八曰施。”[7](这些内容与张源相同)而到了明末黄龙德撰《茶说》时,则进一步指出独饮与跟“茶侣”一起“品茗”感受的不同之所在。他说:“茶灶疏烟,松涛盈耳,独烹独啜,故自有一种乐趣,又不若与高人论道、词客聊诗、黄冠谈玄、缁衣讲禅、知己论心、散人说鬼之为愈也。对此佳宾,躬为茗事,七碗下咽而两腋清风顿起矣。较之独啜,更觉神怡。”
从以上这些文献我们不难发现,古代茶人关于选择“茶侣”的基本要求与思想。第一、茶侣必须是懂茶之人,人与茶品必须相宜、即所谓的不能“饮非其人”。第二,品茗之人需要选择高雅之士,不可赋予粗俗之辈。正如卢仝诗曰:“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谢孟谏议茶歌》)或曰:“此正如美人,又如古法书名画,度可著俗汉手否?”(陈继儒《茶话》)等。第三,品茗时分为独啜与宴客,宴客时茶侣的人数不宜多。因为“客众则喧,喧则雅趣乏矣。”从这些要求及其原因的表述可以看出,“茶侣”的选择仍然来自于人与茶的关系着眼,同样是建立在人与物的关系的基础之上,这里的“当为”之理与上述天道的“当然”之理同构。
至于如何通过“茶”这个载体,“品茗”这种营为,探索、呈现人与人的关系应该如何建立?通过“茶”来揭示人应该如何从“物”的束缚中获得自由,超越“物”的追求、“物”的享乐,达到眼中无“物”,心中无碍的澄明之境等都没有得到体现。特别是对于“茶侣”选择进行人的雅与俗区分,把“雅”的追求放在核心的位置,拒绝“俗”的参与,从而使“茶”成为“轩冕之徒,超然世外者”等“翰卿、墨客,缁流、羽士,逸老、散人”等社会名流、有闲、有钱阶层的垄断性消费。这种规约,显然与“茶道”之“人道”中应该追求“众生平等”的根本精神背道而驰。当然,我们应该承认,作为中国茶文化上升到“品茗”追求的就是源于上述翰卿、文人、墨客、缁流、羽士等所谓的“轩冕之徒,超然世外者”使然。然而,要让“品茗”上升到“茶道”,必须超越个体的身份、地位本身,以“众生”为“茶侣”,进入真正意义的以“茶”问道、以“茶”悟道、以“茶”载道、以“茶”弘道的审美营为,才能说中国茶文化的审美追求达到了“茶道”的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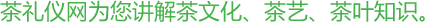




 喝茶敲桌子,是无礼还是有礼?
喝茶敲桌子,是无礼还是有礼? 茶,很慢
茶,很慢 茶艺四要——茶水火器
茶艺四要——茶水火器 茶虽同,味道却不同
茶虽同,味道却不同




